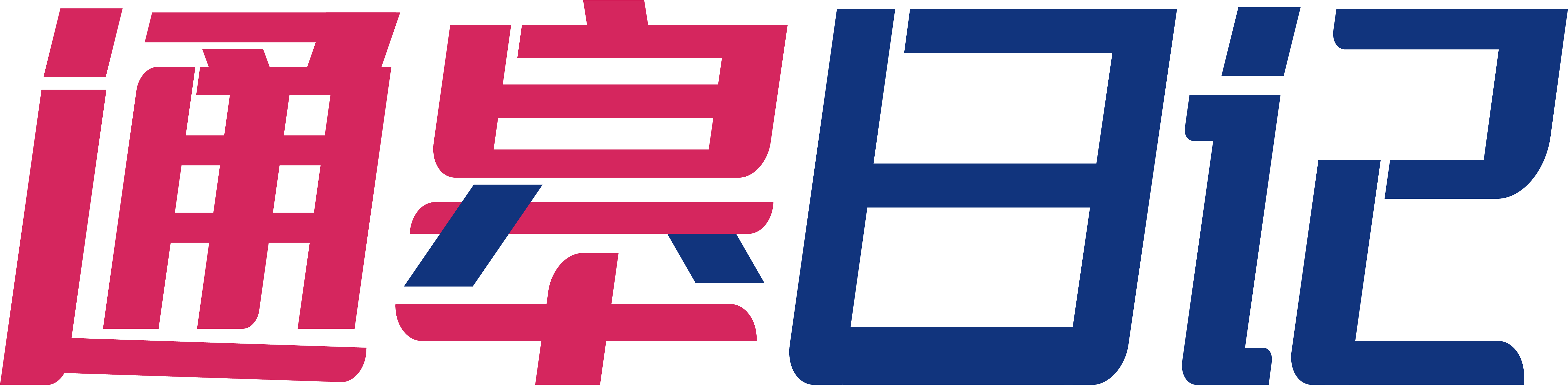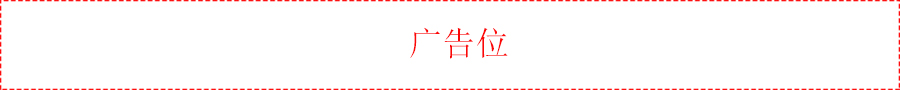烧饼
提起烧饼,如皋人总是有港不完的经——哪儿刚开了一家、哪儿的烧饼最好吃哪一家的烧饼馅儿多、哪一家生意好........

花好月圆摄
可以说,烧饼是如皋这座城的灵魂,从城市到乡郊,从耄耋到孩童,吃烧饼、议烧饼、是美味、是乡愁。
石庄草炉烧饼
石庄个体经营户张松军先生凭着记忆给我们还原了一点草炉烧饼的印象。
小时候,常听老人讲,石庄的草炉烧饼在如皋乃至苏中地区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早年,石庄草炉烧饼、林梓潮糕、白蒲茶干,齐名如皋特产,流传较广。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吋的经济和物质非常匮乏。住在镇东不远乡下的我,也很少能吃上街上的特色小吃。
不过,特殊年代,成全了我有幸见识和品尝过声名远扬的石庄草炉烧饼。

▲当下如皋街头巷尾的烧饼
记得十一、二岁那年,一天上午,我跟着父亲走近路上街。也就是原南石小围墙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进街的。刚到青石板铺就的街面上,就闻到一阵阵扑鼻而来的香味,那香气随风而散,沁入胃蕾,我不禁两眼放光,四处搜寻,咽喉情不自禁咽下泉涌似的口水。当时,南街好象有三、四家烧饼店,所以香味特别浓。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在南石小北边路东停下了脚步。我抬头一看,这是一家门脸朝西的烧饼店,门面没有招牌,木板踏子大门。进得门去,父亲跟老板打了声招呼,当时老板好象叫“大帕”(音),店堂内铺有砖头地坪,地面扫得清洁光亮,一张八仙桌油光发亮,桌面上放有一把瓷质大茶壶和一叠大碗。四、五个上年纪的爷爷辈们围坐在桌旁,一边喝茶侃经,一边悠闲的等着。
门口,倚北山墙砌有一特殊的大肚土灶,炉膛口足有半人高,炉门呈筛子大小的圆形,炉膛呈球形空洞,空间很大,炉灶旁放有几梱麦秸秆和稻草。

▲草炉烧饼的炉子和我们现在常见的桶炉不同
草炉的东边,倚墙放有一张长方形案板,木质的案板上洒满了雪白的面粉,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正在不停的忙碌着。老板中等身材,体型稍胖,见人一脸笑,和蔼可亲。印象最深的是,好象他的前额有一铜钱大小的赘肉。他们一人压坯,一人包馅,双手十分麻利。

▲烧饼的做法也和我们石庄现在的桶炉烧饼差不多
烧饼馅也按时节变化而变换,春季只有韭菜肉碴馅,秋冬季则是萝卜丝馅和野菜油碴馅。而石庄烧饼基本没有甜馅,他们做的烧饼一般有中号碗口大小。
当烧饼坯做好后,一排排平铺在案板上,老板娘用毛刷刷上一层油后,飞快均匀地在面饼上洒上一层白芝麻。
接着,老板围着白围裙,上身打着赤膊,头戴象济公一样的布帽,将一梱麦秸秆在炉心点燃,随着“噼里啪啦”的一阵响,火苗立即腾起,照亮了整个炉膛。连续几梱秸秆烧完,胖老板用手沾点水,洒在炉壁上,凭着经验,试一下炉子的温度。

▲贴烧饼之前要清理炉膛
炉温烧好后,老板用钢叉将死灰翻盖住明火,用以保温。然后老板拿起一条毛巾,迅速在炉膛壁上掸掉烟尘,接着进入贴饼的环节。
只见老板拿起烧饼坯子,在手上左右颠两下,让饼底湿润一下,因为炉温高,所以动作要快,由近及远,开始将一块块烧饼坯子向炉壁贴去。当贴到炉顶部和深处时,人的半个身子都要探进去了。

▲贴草炉烧饼非常辛苦,上半身要钻进高温的炉腔
烧饼贴好后,老板己被炉火烘得满头大汗。他顾不得擦把汗,立即开始加温了。这时,火候的掌握就成了非常关键,火大了会烤焦烧饼,而火小了,又烤不熟。
这时,老板引燃了一梱稻草,因为稻草比秸秆熬火时间长。老板不时用钢叉将燃烧的稻草上下扬起,为的是将炉温在整个炉膛保持平衡。一阵忙碌后,散发着芝麻的香味,从炉膛内迅速飘出。

▲桶炉烧饼以煤炭为燃料,草炉烧饼都是用麦秸做燃料
火候已到,老板一手拿着长柄铁铲,一手举着长杆铁网兜,铲起饼落,兜满则倒进一旁的蔑制竹匾内。

▲烤好的烧饼也和桶炉烧饼有点类似
望着油黄黄,涨鼓鼓的落炉烧饼,我早已忍耐不住。胖老板,及时用夹钳,夹了两个烧饼放在了我和父亲面前。我不顾烧饼的滚烫,左右手不停的交换着,小嘴再也控制不住咬上一口,烫得我直咧嘴吸气……,这样的烧饼吃起来特别有滋味。另外,吃烧饼特别爱吃烧饼屑子,那个脆香简直无法比喻。
俗话说,乡下人吃不到落炉的烧饼,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烧饼讲究的是现做现吃,落炉的烧饼干香松脆,面黄里酥,油而不賦。而冷了的烧饼则软韧难咽,酥和香荡然无存,烧饼也就自然失去了吃头。
后来,随着桶炉烧饼的兴起,传统草炉烧饼失去了竞争优势,石庄的草炉烧饼在七十年代末,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再后来电烤箱的问世,电炉烧饼更冲淡了石庄人对草炉烧饼的记忆。
现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想起石庄的草炉烧饼,仍然念念不忘。那是石庄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却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实在令人遗憾!